中新社北京9月9日电 题:陆天明:反腐电视剧编剧的“理想主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陆天明已写作超过50年,其最让人熟知的身份是小说《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反腐电视剧编剧、作家以及知名导演陆川的父亲。不久前,他出版了“中国三部曲”之二《沿途》,他想要为一代人立传。
我们这代人对时代有话要说
陆天明想告诉人们,曾有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崇高和无私为己任。下决心酝酿“中国三部曲”时,陆天明正“火”。《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几部反腐热播剧使他和周梅森、张平一起被称为中国反腐剧的“三驾马车”。几乎每个月有人来敲门,说“你给搞一部电视剧吧”,只要陆天明点头,资金是现成的。
电视剧带来的收益,远大于纯文学创作。但他不想再写电视剧,他总有一种预感,可能来不及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自己没有时间了。70岁时,他已出版9部长篇小说,担任编剧的几部电视剧拿遍了中国电视剧的各类奖项,他决心停下所有的创作和任务,把剩下的这点时间留给自己,写一些心里话,写一部“如果再不写就来不及了”的小说。
“中国三部曲”展现了谢平、向少文、李爽三个上海知识青年几十年间的人生沉浮。三部曲之一《幸存者》讲述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带着纯真的理想主义投身边疆建设经历的磨砺与伤痛;此次出版的三部曲之二《沿途》承续上一部的脉络——尘埃尚未落定,崭新的时代来临,他们又从西北边地回到京沪等大城市。陆天明在扉页中写道:“我们这代人一切的幸与不幸都缘于我们总是处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漩涡中。”
作家们的处女作往往是写自己,陆天明的第一部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就有自己的经历和影子。在写过一系列经济、反腐、军事题材小说之后,他让自己的封笔之作回归到写自己,“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代人对这个时代是有话要说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是第一批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建设的青年学生之一,他们带着纯真的理想——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报名要求16岁,陆天明偷偷修改户口本,且注销了上海户籍,他没想过再回上海,14岁少年心里惦记的就是要扎根在农村。在安徽农民家,苦得紧、干得累,每天的伙食只有两碗稀饭。不到三年,这个年轻人就累垮了身体,因为吐血被特批调回上海。养病的三年,他上午去街道团委工作,下午就泡在上海图书馆,文学功底得益于这段时光。图书馆里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也成为他的精神补给,他后来对比了俄罗斯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差异,后者强调实现自我满足,而前者的主流价值观是为整个国家和民族谋幸福。于是,养好病的陆天明又开始不安心,听说新疆兵团要动员10万上海青年支援边疆,他像是弥补遗憾般地报了名,跑到更远的新疆火焰山。
当时要先坐没有卧铺的火车五天五夜到乌鲁木齐,再往西240公里,才到达他所在的农场。当时动员去新疆兵团,3万人报名才批准1万人,不少人写“血书”,要求走。他在农村的寒潮中发高烧,退烧醒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秧苗怎么样了”。伤痕文学将他们描述为受害者,他觉得并不全面。“我们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几番思索后,陆天明这样复杂地定义这代人,“我们经历的事情只有我们来说,我们不说,别人说不准确,可能也说不了。”这样才会有“三部曲”,他在小说里折返历史现场,以自身参与和见证的经历,试图把当年的理想诠释清楚,讲给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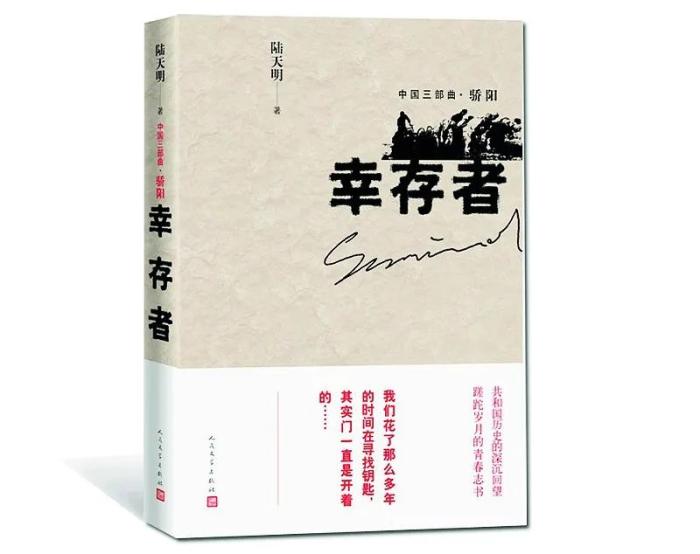
“写作不能脱离社会”
新疆的条件比安徽更苦,最初的日子,陆天明和另外十几个上海去的男生一起住半地窝子,睡在铺着麦草的地上,但精神上感到开心且坚定。他在农场安家、结婚、生子,成了地道的西北人。1971年出生在新疆奎屯的陆川回忆起那段童年生活时,仍然记得父亲的喜悦和力量。
1971年,陆天明向农场领导请了七天假,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躲在一个不能生火的仓库,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四幕话剧《扬帆万里》。1974年,这部话剧代表新疆进京汇演,获得巨大反响,他和全家因此被调入北京,进了广电部大院,成为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的一员。在陆川印象里,那时的父亲是一个总沉坐在书桌前的背影,稿纸写了一摞又一摞,名字开始出现在《当代》《收获》这样的文学杂志上。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搓麻将,也不上山头不进圈子,写作以外的时间,他跑去炼钢厂下生活,要么去法院跟着老法官办案子。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观,他认为作家并非不能强调自我,但基础是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他发现自己心里还是青少年时期被强烈灌输的“天下为重”“民族大义”“国家大事”……从那时起他给自己定了一条座右铭:“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后来一系列反腐小说诞生的内因。
中国第一部反腐剧《苍天在上》的波折,是一个他讲过很多遍的故事。1992年,已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编剧的陆天明接到任务——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本。他回忆,那时,反腐是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的话题,陆天明觉得写什么都不如直接写老百姓关注的痛点和热点。
闭门5个半月,他完成了《苍天在上》,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展现一位副省级干部的经济犯罪。几经曲折,该剧1995年2月开拍,同年底播出。这部极富开创意义的中国首部反腐剧引起巨大轰动,在央视黄金档播出时单集收视率最高达到39%,至今也极难超越。此后,陆天明连续推出《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等作品,无一不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但文学圈却反应矜持。陆天明感慨:“那时候有些朋友颇瞧不上写电视剧的作家,认为他们做的不是纯文学,不够‘阳春白雪’,但影视能让作品直接进入广大民众的视野,让我意识到写作不能脱离社会。”

我们都是“半度人”
陆天明有些倔劲儿,曾公开表示不应该让那么些优秀作家去当大大小小的作协官员——“现在我们不缺官,缺的是好的作家和作品。”当年《苍天在上》被几个部门要求修改,他怎么都不肯屈服。陆川考电影学院研究生,他也不愿走关系。“没必要走后门去搞艺术,艺术这东西靠爹妈是不行的。”
他的倔里有理性。他喜欢分寸感,生活中他不干预儿子的生活和创作。他不喜欢太黑暗的作品,生活已足够沉重,非要在最阴暗的地方挖伤疤,在他看来不是本事,而是发泄情绪,作家的眼睛应向前看,给人以希望。为一代人立传,最大的难处就是“完全写真了是行不通的,掺假了更不行”。
《桑那高地的太阳》里,对边疆全力奉献赤诚却一次次被他所依赖、热爱的人们打翻在地的“谢平”,的确是陆天明掏心掏肺把自己化在了其中的人物,所以新书《幸存者》《沿途》中,主人公又使用了这个名字。陆天明回忆:“写作时,那些过往、经历都冒了出来,经常是写着写着,眼圈就红了。”他给自己定下两个原则:一是真实,不跟着别人的调子走;二要避免片面和偏激,也就是要以正确的判断写出来。

长期游走在“当年的我”与“站在正确客观角度呈现的我”之间,他常常有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在小说里,生活让谢平真切地感到自己在变。如何顺势而为,又如何坚守?谢平有个笔名叫“半度人”——“我们都不完美……都是半度人。”在陆天明笔下,面对理想主义时,也并非只有两种结果——信仰或者不信仰,人们无法获取终极真理,但总在接近真理的沿途中。这是另一层面的“半度人”。
写完《沿途》,陆天明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因不能久坐,朋友送给他一个升降写字台,站着写,写一阵儿就活动活动。陆川曾在微博上回忆父亲的写作生涯:每天半夜两三点爬起来写,写到天亮,出去跑步,回来洗个冷水澡,然后写上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早早休息……老爷子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陆天明给自己制订了更科学的作息时间,早晨四五点起床,白天写作,晚上九点钟准时上床睡觉,为了保重身体。“我还要写完第三部呢!”三部曲的前两部一共用去11年,他希望最后一部不会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