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6日电 题:沈斐:中国“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有何不同?
作者 樊中华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基本理想。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共同富裕”,还写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
与此相较,肇始于乌托邦的西方“福利社会”思想及其实践也由来已久。
一个是中国的阶段愿景,一个是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国“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异同何在?中国又能带给世界怎样的全新答案?
为此,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斐。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新社记者:中国“共同富裕”和西方“福利社会”的发起背景和实质有何不同?
沈斐:进入马克思主义视野可以看到,二者发起的背景和实质完全不同。
中国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是在消灭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级”阶段的任务。它将进一步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通过共同富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西方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目的是以拉动需求对治过剩性危机。它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以美国为震中、席卷整个西方的“经济大萧条”。为拯救美国,罗斯福出台“新政”,以高额累进税、社会保障政策和“计划经济”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劳资矛盾和重启经济。“新政”成功后,凯恩斯经济学传播开来。在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压力下,欧洲开始推行国家福利政策,建成一批福利社会。
《资本论》第二卷深刻揭示了其实质:为实现剩余价值,资本的流通过程要求抬高工人工资,让工人阶级的需要成为社会有效需求,让大规模消费成为资本周转和循环的推动力——这后来成为凯恩斯经济学暗中依据的一条原理,也是福利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石。

按照《资本论》中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福利社会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次自我否定——从自由市场中内生出政府干预的要求,让利润至上的资本家阶级“自觉牺牲”部分利润以换取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运转。
中新社记者:以“高福利”为标识的西方福利社会制度为何频遭危机?
沈斐:福利社会一度缓和了贫富差距,克服了过剩性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爆发的滞胀危机是福利制度运行遭遇的一次重大危机。“高福利”意味着高工资,与资本家追逐高利润天生矛盾。因此资本家用两种方式对抗“高福利”:一是大量企业外迁,寻求海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市场,导致西方实体经济“空心化”;二是企业股份化发展,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虚拟经济领域,致使资产价格虚高。二者叠加,引发“滞胀”。
为克服“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让福利制度再遭危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否定凯恩斯主义,抽掉了“高福利”的理论根基;在政策上又削减“高福利”,导致西方福利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停步不前。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金融化发展,又引爆了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欧债危机,让西方“高福利”更加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而福利社会“高福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大众消费以解决过剩问题,这让西方步入“消费社会”,问题丛生:一是大规模消费和过度生产造成滥用资源、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二是把人变成消费机器,造成物化的、片面发展的人;三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供给”几乎都集中在物质层面,即便是教育、假期等也是暗中为消费服务,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失衡。
中新社记者:中国此次提出的“三次分配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分配制度有何不同?
沈斐:西方的三次分配与税收激励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联。在不少西方国家,若主动捐赠收入所得,即可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税,或享有社会保障方面的某些优待。因而西方的慈善捐赠行为,固然有宗教、道德、伦理的社会土壤,也不乏避税、利益输送、收买人心等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虑。
中国的“三次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相联系,不仅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也是完善分配体系、促进社会公平的探索。改革开放40多年,对于先富的群体,在其自愿的情况下,理应打开通道,为其社会责任转向提供便利。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提出三次分配正当其时。
也因此,一些研究将中国与西方简单比较,得出中国的慈善捐赠活动还很不够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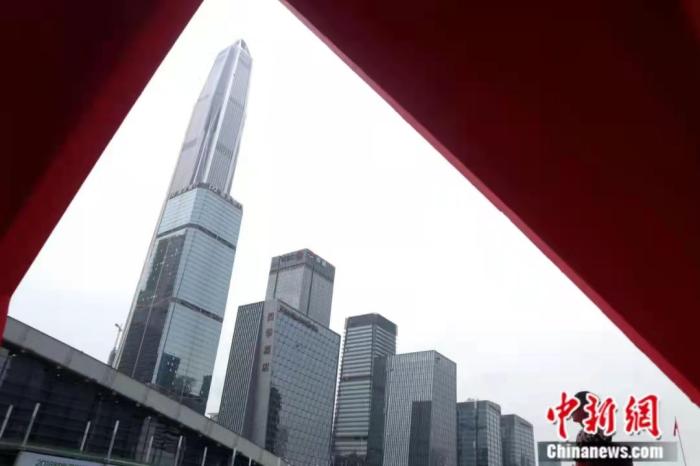
中新社记者:实现共同富裕被称为是全球性的治理难题,中国信心何在?
沈斐:这一全球性治理难题对西方和中国来说性质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天然要求“相对贫困”,要有人失业,经济才有效率。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财富的同时也制造贫困。对资本主义来说,缩小贫富差距不过是发展的权宜之计,谈共同富裕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必须也必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全新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共同富裕的第二步。
可以说,西方走向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迫于发展压力的自我革新,过程非常痛苦曲折;而中国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一以贯之的自觉奋斗和追求,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新社记者:实现共同富裕,对中国来说挑战何在?
沈斐:挑战在于能否实现全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与资本主义以“资”为本、用钱衡量一切的价值观不同,中国的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取向,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自主性、创造性、自我实现的程度为价值尺度,将发展的目的回归人本身,而不仅聚焦经济增长。
共同富裕的内涵远超物质层面,因此不能简单量化考核。在建立以人本价值观为基础的多元价值衡量标准体系方面,我们还需继续探索。
此外,中国经济的飞跃最初发生在法制、政策尚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因此更应关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初次分配”,通过健全完善法治、政策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体系,从根本上消除各种不是凭借劳动、管理和创新产生的牟利行为。
中新社记者:西方福利社会发展已有近百年历程,是否有经验可供参考?
沈斐:西方一些先进制度和政策,如不同发展阶段的税收及税收激励体系、慈善捐赠的信托制度体系,及其在运作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值得学习借鉴。
如《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主张增收财产税和资本税以降低资本收益的份额,提高劳动者收入比例;又如今年3月美国桑德斯联合民主党参议员提出的《为了99.5%法案》,揭露了“信托是美国富人规避税收,实现财富代际转移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对于中国完善信托法律制度、加强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组织工作制度有警示意义。
我们还需警惕“福利社会陷阱”,即与消费社会伴生的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撕裂和片面发展。20世纪50、60年代,“战后婴儿潮”的年轻人将精神寄托在以迷幻药、摇滚乐为特征的嬉皮士文化中;滞胀危机后,西方人用“新社会运动”这种虚幻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物质满足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需求,形成了“白左”的政治正确。对中国来说,共同富裕是“五位一体”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景。这一点上,福利社会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受访者简介】
 沈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
沈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
主要兼职: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治经济学专委会副秘书长。
主要讲授:《资本论》导读、《共产党宣言》导读、百折不回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重温党史,坚定初心、苏共兴亡对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启示等。
上海市2021年“党史学习”、2020年“四史学习”宣讲团专家成员;自2019年起,连续5期应邀赴中央党校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的中青班授课。2019年获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